它,伤了我
2016-08-07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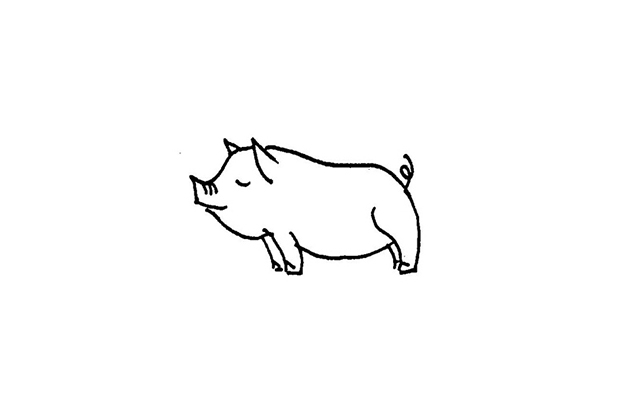
对于记忆的真实性,我不敢百分百的相信,因为没有了当时身临其境的感受,一切都会变的虚无。但有些记忆不同,它们是有证据的,每当这些证据出现,我的大脑都会犹如穿越般将我带回到过去事情发生的那一刻,这些证据有可能是一串文字、一首歌曲、一张图片、一个饭馆、一场大雨······当然也有可能是一块伤疤。
说到伤疤,这个每个人身上都会有,我观察过好多人,基本上伤疤都是在关节处居多,比如胳膊肘、膝盖这些地方,这或许是因为这些地方经常裸露在外面的原因,很容易磕着碰着,当然他们有可能其它的地方伤疤也很多,但我只能看到这些,所以观察别人是受限度的。
而观察自己就容易多了,想观察哪就观察哪,我看遍了我全身的旮旮旯旯儿,我发现我和其他人一样,好多伤疤也都是在关节处,但有些就比较隐蔽了,比如咯吱窝、胸前、胯部、屁股、大腿根、脚底······
细数这些伤疤有小有大,有深有浅,最大的就是右咯吱窝处的那个长10多公分,宽半公分左右的长条疤,记得这块疤是在我11 、2岁的时候被铁丝刮的,当时好像被刮掉了一条肉,现在想起来已经不是疼的感觉,而是一种全身都不自在的感觉,不过还好胳膊没什么事,只是留下一条长长的疤。
而最深的就是我两只脚脚底的那已经看不讨清楚的疤,当时我大约7、8岁的样子,我去隔壁院子玩,结果一只脚扎上了一根水泥钉,一只脚扎上一根输液针头,扎上的时候估计脚瞬间麻木了,我都没感觉到,直到到家脱鞋脱不下来时我才发现鞋底有东西,现在想想还是那种全身都不自在的感觉。
但如果按伤的后怕的程度来讲,最大的和最深的伤都不能排上榜首,因为后怕是一种联想过后的恐惧,像是咯吱窝和脚底的伤经过最坏的联想过后,最多就是我的胳膊因肌肉和神经组织受损无法正常运动,我的双脚因感染而被截掉,但是我一样可以活着。后怕的伤是关于生命的,一种是生命的继续,一种是生命的延续,对于我来讲最让我后怕的伤是关于生命延续的,而这个伤不是我一个人造成了,还有一头猪。
事情大约发生在我7、8岁时的样子,那时正值春季,村里的人们都在忙着播种,我们家也不例外,老爸老妈白天忙着田地里的播种,早晚还抽空忙着家里房前房后菜园子的播种。房后的园子挺干净的没什么要收拾的,用铁锹重新挖一遍,打上池子蒙上地膜就可以种菜了。
房前的园子因为每年秋天收回的玉米都需要有个地方放,而且不能直接放在地上,所以就在园子两边各搭了一个棒架,棒架的结构很简单,就是在地上栽4根桩围成一个矩形,然后用粗的木头横横竖竖的搭在桩上,最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细的榛柴杆将大的缝隙遮挡住就可以了,棒架有两个好处:一是可以加速玉米的风干,二是可以减少老鼠的偷吃,所以村子里每家每户院子里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棒架,待到秋收过后登上山顶俯瞰整个村子,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黄色色块从村东头一直排到村西头,整个村子完全就是一片黄色的海洋。
棒架上的玉米通常在冬季的几个月里会被一种叫做niao棒机的东西处理掉,那是一种手动的机器,一边是摇把,一边是带着密密麻麻尖锥的转盘和铁罩,铁罩与转盘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玉米的大小进行调节,顺时针转摇把玉米就会往下走,逆时针就会退出来,这种机器比起最早的用锥子一个一个玉米的戳方便多了,但是种机器处理出来的玉米仍然不能将玉米粒全部弄下来,所以之后还得用手一根一根的将处理出来的玉米重新在尅一遍,但即使这样,那时村子里每家每户基本上都会有一台。
玉米处理完了,棒架也就是去了它存在的意义,老爸老妈收拾完了房后的园子,就开始收拾房前园子里的这两个棒架,说是收拾其实就是拆,一边拆一边将那些榛柴杆和木头又归回了拿时的位置,因为秋天收玉米时还要重新搭,所以老爸将那4根桩留在了那里没有拆掉,而这也就为之后我与猪之间发生的事情留下了伏笔。
小时候家里每年都会养猪,而那一年我们家养了一只大黑猪,因为猪圈里比较脏,所以每次喂它的时候老妈都会把猪食放到猪圈门口的石槽里,然后打开门让它出来吃,有时候老妈比较忙没法看着它吃食就会叫我过去看着,那只猪一般吃完食后就会躺下来让你给它挠痒痒,那时家里没有养猫也没有养狗,所以我就把它当成了宠物一样,它喜欢挠痒痒我就给它挠,每次给它挠的时候它都是闭着眼睛,一脸享受的样子,时间慢慢的走着,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一点点的变的紧密,后来老妈喂它的时候不用喊我,我自己就会过去看着它吃食,给它挠痒痒,直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天······
记得那一天的天气灰蒙蒙的,虽没下雨,但空气却湿乎乎的,老妈像往常一样把猪食倒进了石槽里,打开了猪圈门,然后就忙别的去了,我也像往常一样赶紧跑过去看着它吃食,等着给它挠痒痒。
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它吃食吃的特别慢,所以我就跑到院子中间玩去了,我一会扒拉扒拉弹球,一会挖挖土,一会拿根小木棍耍来耍去,好一阵子抽风,突然我想来一个金鸡独立,但感觉站在地上太简单了,我环顾了下四周发现眼前的这根木桩就不错,说时迟那时快,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,也就是在这时它也吃完食了,它似乎已经习惯了我给它挠痒痒,朝着木桩上的我就走了过来,而我正一只脚踩在木桩上晃晃悠悠的站着,·它走到木桩的旁边就停了下来,正要失去重心的我看见它宽广的后背,赶紧将另一只脚踩了上去,那一刻的我一只脚踩木桩,一只脚踩大黑猪,手里还拿着一根小木棍,简直就是分分钟征战沙场的节奏,如果有人在旁边一定会被如此的景象给镇住。
但好景不长,当我还沉溺在如此的感觉之中时,它突然侧身一卧躺下了,而我的重心那时都在它那宽广的背上,这一下就把我给闪的不知所措了,我另一只脚出溜就顺着木桩滑了下来,木桩一直滑到我的大腿根,鲜红的血马上就从裤子上渗了出来,眼角也流出了眼泪,我嘴里一边嘶哈着,一边双手捂着大腿根哆嗦,太疼了,我已经忘了大黑猪当时的反应,因为当时我已经顾不上看它了,我甚至忘了之后包扎的事情,只记得那钻心的疼。
现在不但记得那种疼痛的滋味,而且还很后怕,那可是大腿根啊,如果那个木桩再高10公分,或者那时的我长的很矮,我生命延续的功能就彻底的废了,每思至此大腿根都一阵阵的发凉。自那以后,大黑猪吃食我还是回去看着,还是会给它挠痒痒,它还是保持着那种一碰就倒的习惯,而我却不再跑到那木桩练金鸡独立了。
现在家里已经不再搭棒架了,木桩也没有了,更不养猪了,有时候回到家看着院子里盖着的小偏房,空荡荡的猪圈,还有满是水泥的月台······感觉时间过的好快啊,仿佛上一秒我还嘶哈的捂着大腿根,下一秒我就电脑前写这些了。
图片来自网络